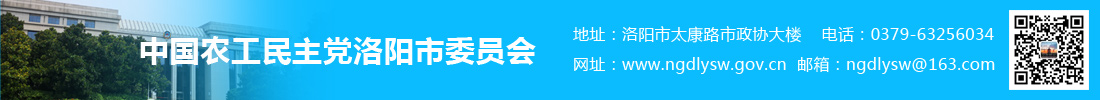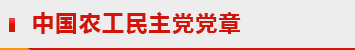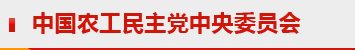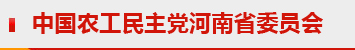农工要闻
- 2023-9-24中国农工民主党洛阳市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 2023-1-18雷雪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郭珈宜 李自强 史明艳 索亚星履职河南省政协委员
- 2022-11-17【学习二十大】市委会主委雷雪芹:学深悟透 深信笃行 引领推进履职实践提质增效?
- 2022-6-2农工党洛阳市委举办2022年环境与健康宣传周活动
- 2022-6-2农工党洛阳市委会、民建洛阳市委会、民进洛阳市委会联合开展“浓情端午,欢畅露营”活动
- 2022-6-1河南省豫西黄河湿地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成立
- 2022-5-28农工党洛阳市瀍河支部开展“传承红色文化 一起奔向未来”六一儿童节活动
- 2022-4-29助力乡村振兴——农工党洛阳市委捐赠医疗设备及医疗物资
- 2022-4-27履职尽责,担当有为——10名农工党党员参加涧西区两会
- 2022-4-11洛阳市9名农工党党员参加洛龙区两会
- 2022-2-25农工党洛阳市第七届委员会第十次(扩大)会议召开
- 2022-1-11情暖人心,共同抗疫

通知公告
- 2022-3-10报废资产处置公示
- 2021-1-29澳门新濠天地:做好2021年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倡议书
- 2020-10-30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发布
- 2020-2-26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手册
- 2020-2-24澳门新濠天地:庆祝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90周年理论 征文启事的通知
- 2020-2-10澳门新濠天地:统计参与抗击新型肺炎党员情况的通知
澳门新濠天地
- 2023-1-18雷雪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郭珈宜 李自强 史明艳 索亚星履职河南省政协委员
- 2022-6-1河南省豫西黄河湿地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成立
- 2022-4-27履职尽责,担当有为——10名农工党党员参加涧西区两会
- 2022-4-11洛阳市9名农工党党员参加洛龙区两会
- 2022-1-4中国农工民主党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支部委员会成立
- 2021-12-29农工党洛阳市委到黄河湿地开展调研
组织建设
- 2023-9-24中国农工民主党洛阳市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 2023-1-18雷雪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郭珈宜 李自强 史明艳 索亚星履职河南省政协委员
- 2022-1-4中国农工民主党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支部委员会成立
- 2021-12-27农工党洛阳市孟津区支部委员会成立
- 2021-12-23农工党洛阳市澳门新濠天地骨干党员参加农工党河南省委澳门新濠天地工作培训班
- 2021-11-17农工党洛阳市委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视频展播
社会服务
- 2022-6-2农工党洛阳市委会、民建洛阳市委会、民进洛阳市委会联合开展“浓情端午,欢畅露营”活动
- 2022-5-28农工党洛阳市瀍河支部开展“传承红色文化 一起奔向未来”六一儿童节活动
- 2022-4-29助力乡村振兴——农工党洛阳市委捐赠医疗设备及医疗物资
- 2022-1-11情暖人心,共同抗疫
- 2022-1-11迎“疫”而上,农工党洛龙一支部党员张学民
- 2022-1-4农工党洛阳市委开展反诈骗宣传进社区活动
支部活动
- 2022-5-28农工党洛阳市瀍河支部开展“传承红色文化 一起奔向未来”六一儿童节活动
- 2022-4-29助力乡村振兴——农工党洛阳市委捐赠医疗设备及医疗物资
- 2022-1-11情暖人心,共同抗疫
- 2022-1-4中国农工民主党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支部委员会成立
- 2021-12-27农工党洛阳市孟津区支部委员会成立
- 2021-12-10农工党洛阳市瀍河支部开展爱心助农活动
提案议案
- 2022-4-27履职尽责,担当有为——10名农工党党员参加涧西区两会
- 2022-4-11洛阳市9名农工党党员参加洛龙区两会
- 2020-9-27提案答复—发挥界别优势 助推健康洛阳建设
- 2020-9-25提案答复—积极建言献策 助力乡村振兴
- 2020-9-1提案落实—推行分餐制,洛阳在行动
- 2020-2-28农工党洛阳市第七届委员会提案议案
专委会活动
- 2021-12-29农工党洛阳市委到黄河湿地开展调研
- 2019-12-7农工党洛阳市委召开专委会2019澳门新濠天地工作座谈会
- 2019-4-4农工党洛阳市委第七届专委会成立
专题活动
- 2022-11-17【学习二十大】市委会主委雷雪芹:学深悟透 深信笃行 引领推进履职实践提质增效?
- 2022-6-2农工党洛阳市委举办2022年环境与健康宣传周活动
- 2022-6-1河南省豫西黄河湿地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成立
- 2021-10-14农工党洛阳市委在重阳节组织老党员参观孟津区生态环境建设
- 2021-9-16农工党洛阳市委对口孟津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仪式在孟津举行
- 2021-8-21“疫”线事迹—农工党洛阳市委机关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机关建设
- 2022-4-29助力乡村振兴——农工党洛阳市委捐赠医疗设备及医疗物资
- 2022-1-4中国农工民主党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支部委员会成立
- 2021-12-27农工党洛阳市孟津区支部委员会成立
- 2021-10-9农工党洛阳市委会组织收看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
- 2021-5-14农工党蚌埠市委来洛调研
- 2021-3-9农工党洛阳市委到洛阳轨道交通1号线开展视察慰问活动
文明创建
- 2022-1-4农工党洛阳市委开展反诈骗宣传进社区活动
- 2021-7-22农工党洛阳市文艺支部组织党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 2021-7-22农工党河科大二附院支部组织党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
- 2021-4-30农工党洛阳市自贸区支部开展“五一”慰问活动
- 2021-4-28农工党洛阳市委召开“学五史、守初心、迎百年”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
- 2021-3-9农工党洛阳市委到洛阳轨道交通1号线开展视察慰问活动


健康园地
- 2021-1-29澳门新濠天地:做好2021年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倡议书
- 2011-4-4按时晚餐有益健康
- 2011-4-4“小恶习” 危害“大健康”
- 2010-10-21秋天洗脸最应该注意10误区
- 2010-10-21胡萝卜三种吃法更营养
- 2010-10-21正确泡脚养生 胜过诸多补药
文化广场
- 2022-6-2农工党洛阳市委会、民建洛阳市委会、民进洛阳市委会联合开展“浓情端午,欢畅露营”活动
- 2019-3-25摄影欣赏
- 2019-3-25王华莹书画
公开公示
- 2024-3-122024年农工党洛阳市委会部门预算公开
- 2023-10-102022年农工党洛阳市委会部门决算公开
- 2023-2-72023年农工党洛阳市委部门预算公开
- 2022-9-202021年农工党洛阳市委部门决算公开
- 2022-3-112022年农工党洛阳市委部门预算公开
- 2021-9-20农工党洛阳市委2020年度部门决算
农工党洛阳市委官方微信